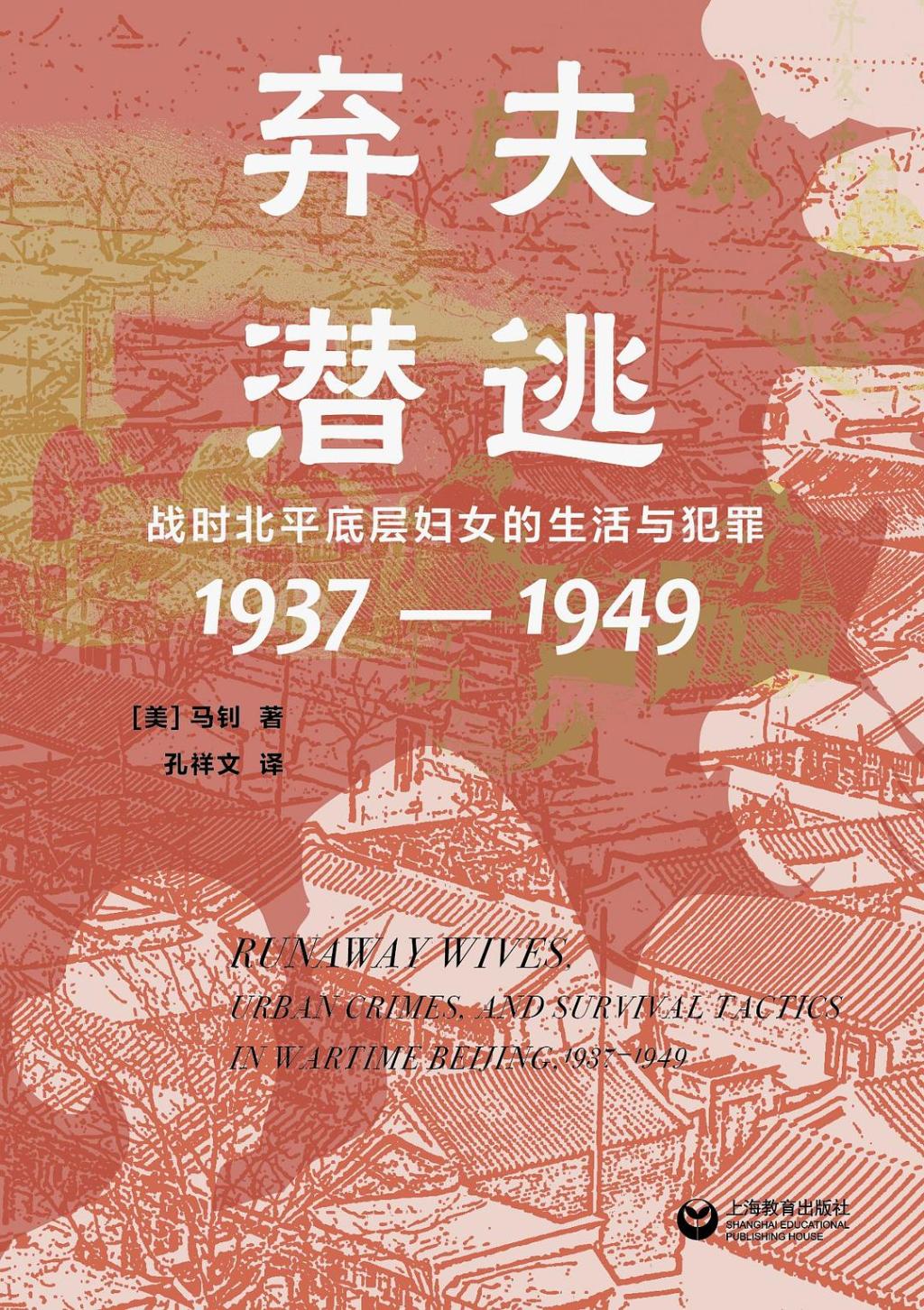
《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美]马钊著,孔祥文译,上海教育出版社|万镜MirrorForest,2025年5月出版,384页,78.00元
1945年春,汪伪政府统治下的北平正处于剧烈的经济与社会动荡之中。3月6日早晨,朝阳门内大街153号福顺号烧饼铺的伙计孙士春焦急地等待着彻夜未归的妻子孙李氏。她于前一天称要回娘家,却一整夜未归,这显然非同寻常。于是,孙士春选择报警。警察调查发现,几日前孙李氏与婆婆发生激烈争执,夫妻因此被逐出家门,自立门户。然而,在缺乏婆家支援的情况下,孙李氏开始担忧丈夫卖烧饼的微薄收入难以支撑一家生计。她遂找到邻居梁赵氏,请求后者帮忙“另嫁一人”。梁赵氏经不起她的软磨硬泡,最终请附近切面铺掌柜李金和牵线,介绍自己的侄子李凤来给她认识。3月5日,在邻居的协助下,孙李氏与李凤来经由火车站逃往后者的老家枣强。然而第二天,警察便将他们二人抓获归案。
两个月后,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若是在清代,依《大清律例》“若夫无愿离之情,妻辄背夫在逃者,杖一百,从夫嫁卖”,孙李氏将面临严厉惩罚(110页)。但在1945年的民国,这类行为已不再属于刑法制裁范围。法院认定孙李氏与李凤来之间既不构成通奸也不涉及重婚,而邻居梁赵氏亦不构成拐骗妇女罪,因为出逃是出于孙李氏的自主意愿。这个案例不仅体现了民国司法在处理性别议题上的观念转变,更揭示了战乱时期社会底层妇女在面对经济崩溃与家庭危机时的求生手段。这也正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东亚系马钊教授《弃夫潜逃:战时北平底层妇女的生活与犯罪(1937—1949)》一书所描绘的时代景观。
近年来,围绕女性社会地位与家庭角色的议题频繁地登上热搜,舆论场上的热议表明,在女性地位不断提升、女性主义理念被逐渐普及,性别矛盾日益加剧的当下,我们亟须对女性的身份与角色进行重新思考与定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回过头来看《弃夫潜逃》所聚焦的日伪统治与解放战争时期北平下层妇女的日常生活,看该书通过对民国时期刑事审判案卷的细致梳理,以深入浅出的写作手法,揭示底层女性所面临的家庭困境,探讨她们如何通过自身的生存“手段”,在法律与制度的空隙间艰难谋生。这部作品处处展现了马钊博士作为历史学者对时代变革中个人生命经验的关怀。无论是对专业历史研究者,还是对更广泛的公众读者来说,这都是一部值得关注、引发共鸣与思考的历史书写典范。
尽管《弃夫潜逃》在中文世界问世仅仅数月,但值得一提的是,它的英文原著Runaway Wives, Urban Crimes, and Survival Tactics in Wartime Beijing, 1937-1949(中文直译为“逃跑的妻子:战时北京的城市犯罪与生存手段,1937-1949”)是在作者200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于2015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发行。因此,我们在讨论本书的成书背景时,不仅要着眼于当下中国的社会背景与学术生态,也应该回到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英文世界的学术脉络中,去理解它的问题意识与研究贡献。在这一时期,北美的中国史研究,经历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社会史转向,“以中国为中心”、立足中国历史与社会内在逻辑的研究方法已经深入人心;再加上中国内地档案馆的对外开放使得利用档案文献,特别是司法档案,聚焦庶民社会,以自下而上的视角研究中国史的趋势日益兴起。与此同时,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史研究受到文化人类学、语言学转向影响,开始关注隐藏在宏大社会结构之下微观的个体经验与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会性别史的兴起,将性别权力关系引入历史分析范畴,把女性视为能动的历史参与者,而非仅是革命叙事中的受害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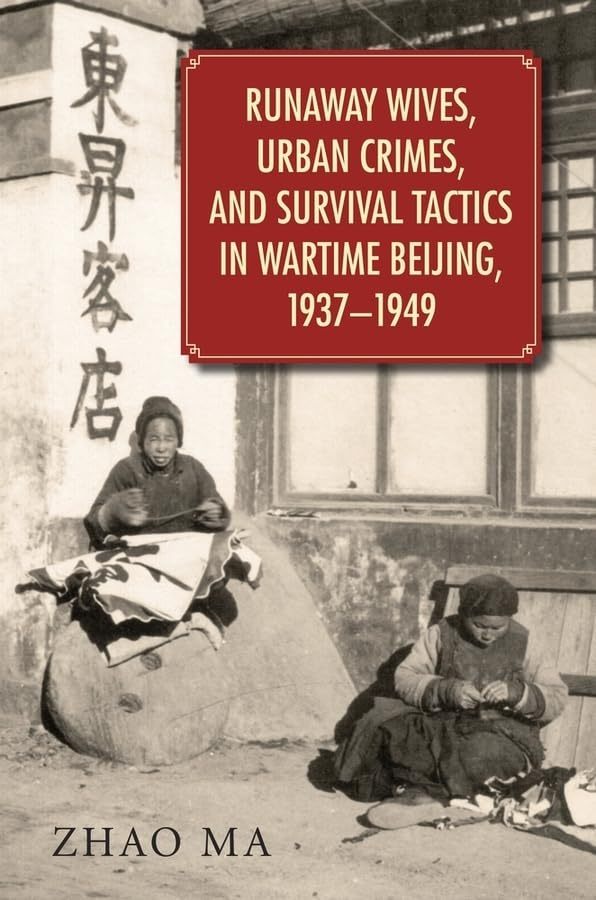
《弃夫潜逃》英文版
与此同时,马钊博士彼时就读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正处于这场史学转型的核心地带,他的两位导师——罗威廉(William Rowe)与梅尔清(Tobie Meyer-Fong)教授,一位是北美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另一位则是运用新文化史方法研究明清史的代表性学者。二十一世纪初北美中国史研究的脉络与本书作者的自身的学术谱系,几乎决定了《弃夫潜逃》必将是一本兼具社会史研究方法与文化史问题关怀的著作。一方面,作者继承了导师罗威廉教授对城市社会史的关怀,从民国时期北京地方法院的刑事审判档案入手,探讨战时的城市空间、社会治理以及女性的职业、犯罪与经济状况;另一方面,该著借由法国文化理论家米歇尔·徳·塞托(Michel de Certeau)所提出的“手段”(tactics)这一概念,探讨底层女性在时代裂变的历史环境中谋求生存的个体经验。
在我看来,《弃夫潜逃》一书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作者突破了主流民国史研究对政治事件的关注,借助对司法档案的仔细分析,拨开了启蒙与进步叙事的迷雾,带我们窥见战时北平下层女性真实的日常生活,剖析她们如何通过对城市空间、邻里关系、婚姻与家庭关系、社会习俗等仅有“资源”的理解与利用,在法律与制度之间为自己争取出十分有限却仍然有效的生存空间。正是在这些微观的个体行动中,作者揭示了改革与革命带来的制度与观念变迁怎样影响底层妇女的经历,也展现了后者如何通过自身的生活实践与犯罪行为,促使国家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市的社会与道德结构(31、285页)。
不过,与其将《弃夫潜逃》视为一部纯粹的性别史著作,我更倾向于把它定位为一部关注制度变革、城市发展与个体经验之间关系的社会史研究。就像作者所指出的:“妇女身份与城市空间的建构不仅由性别关系所决定,还同时带有鲜明的阶级特征。”(30页)与许多聚焦于性别角色建构与权力关系的社会性别史著作相比,这部著作的视野更为宏阔。它以底层女性为历史主体,从她们的日常处境出发,辐射到战时北平城市社会的多重面向。因此,尽管我在前文提到,《弃夫潜逃》的付梓回应了当下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广泛关注,而且目前公众媒体中所能见到的关于它的讨论多集中于妇女议题,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单一的妇女史著作。它更应被视为一部融合城市史、法律史与妇女史等学术视角的社会史研究。如果忽视了这些议题上的多重维度,我们对这部书的学术贡献的理解也势必会被削弱。
举例来说,本书第一章便通过对下层妇女劳动状况的考察,呈现了战时北平的社会经济结构与职业观念。作者不仅探讨了女性如何依靠零工与灰色经济应对生存危机,还进一步揭示了北平城市经济结构对女性就业机会的限制。由于工业化进程缓慢,城市内正式岗位稀缺,妇女在工业与商业领域中可获得的工作机会极为有限。作者借助当时的社会调查资料指出,北平社会普遍认为妇女应当留在家中从事农业劳动,而非外出做工。正因如此,许多年轻女性在工厂短暂工作后便结婚离职,已婚妇女则通常不参与正式劳工市场(62-63页)。
此外,作者还细致考察了“职业”一词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文语境中的语义演变。尽管该词早已有之,但其现代意义的确立与频繁使用主要出现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45-47页)。国民政府当时将“职业”界定为“直接、间接取得金钱或实物报酬之作业”(50页),并将其与“既有生产力、又符合社会道德要求的有偿劳动”联系起来(51页)。随着职业教育的推广,这一原本中性的词汇逐渐被纳入民族解放与妇女运动等更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中。作者认为,“职业”语义的转变不仅为当时社会提供了重新理解劳动与性别角色的新语言,也体现出妇女工作在国家意识形态中被逐渐政治化、国家化的过程。这一文化史取向的语义分析,既为后续章节中讨论女性弃夫离家处境铺垫背景,也体现出作者对语言与思想在社会变革中作用的关注。
本书的另一个重要分析维度是司法观念与实践的演变。在第二章中,作者通过分析判决与法律条文中对男性在家庭中的供养义务的界定,揭示了民国时期官方家庭观念的转变,以及这一转变对弃夫潜逃案件裁判的影响。在传统观念中,丈夫被认为是家庭供养者,而妻子则被相应地视为“受抚养者”。因此,战时北平那些选择弃夫潜逃的下层妇女,并非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那样意在挑战男性权威,而往往是出于抗议丈夫未能履行他们的供养义务(95页)。然而,1930年和1931年颁布的《民法》明确规定:“因负担抚养义务而不能维持自己生活者,免除其义务。”(115页)这表明,当时的法律已经不再将男性视为当然的供养者,亦不将女性视为被供养者。通过对供养义务的重新界定,法律在制度层面鼓励女性追求经济独立、自主谋生,促使她们从家庭中的附属地位中逐步脱离出来。通过对家庭供养关系的再定义,《民法》实际上摒弃了清朝法律中将弃夫潜逃入罪的立法原则——认为这是一种挑战家庭权威的行为;因此,弃夫潜逃不再被视为一种犯罪,女性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的行为由此得到了法律层面的支持与保障。
在此基础上,本书第六章对司法审判中妇女性行为裁决的分析,进一步揭示了战时北平司法实践与性别观念之间的互动。作者借助黄宗智对《大清律例》的分析指出,在清代法律体系中,女性通常被视为“消极的抉择实体”(passive agency),面对男性的追求,她们要么反抗,要么顺从,但其行为始终只是对男性主动性的被动回应。而在民国法律框架下,女性则逐渐被当作具备自主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刑事主体(291页)。然而,制度层面的变化并不必然带来民间观念的同步转型。1945年7月杨占英离家出走案可以说是一个明证。在这一案件中,杨与二十二岁的男友张克贤私奔,藏匿于后者姐夫家中。杨母因为猜测二人已经发生了性关系,羞愤之下报案控告张克贤“拐卖妇女”。她不仅将张描绘为惯于诱骗妇女的危险人物,还坚持女儿出于“家教严格”而无力反抗,是被张用淫威所逼迫。这一控诉手段,表面上是对女儿“清白”的捍卫,实则是通过重申她的“贞洁”与“被动性”来博取法律与社会的同情。在这一过程中,母亲的行为看似动用了法律工具维护女儿权益,实则进一步压缩了女性作为具有自主选择能力个体的社会认知空间。这一案例不仅生动展现了司法制度改革与民间性别观念之间的错位,也显示出女性亲属在现实困境中试图借助法律与道德之间的模糊地带,为“体面”讨回空间的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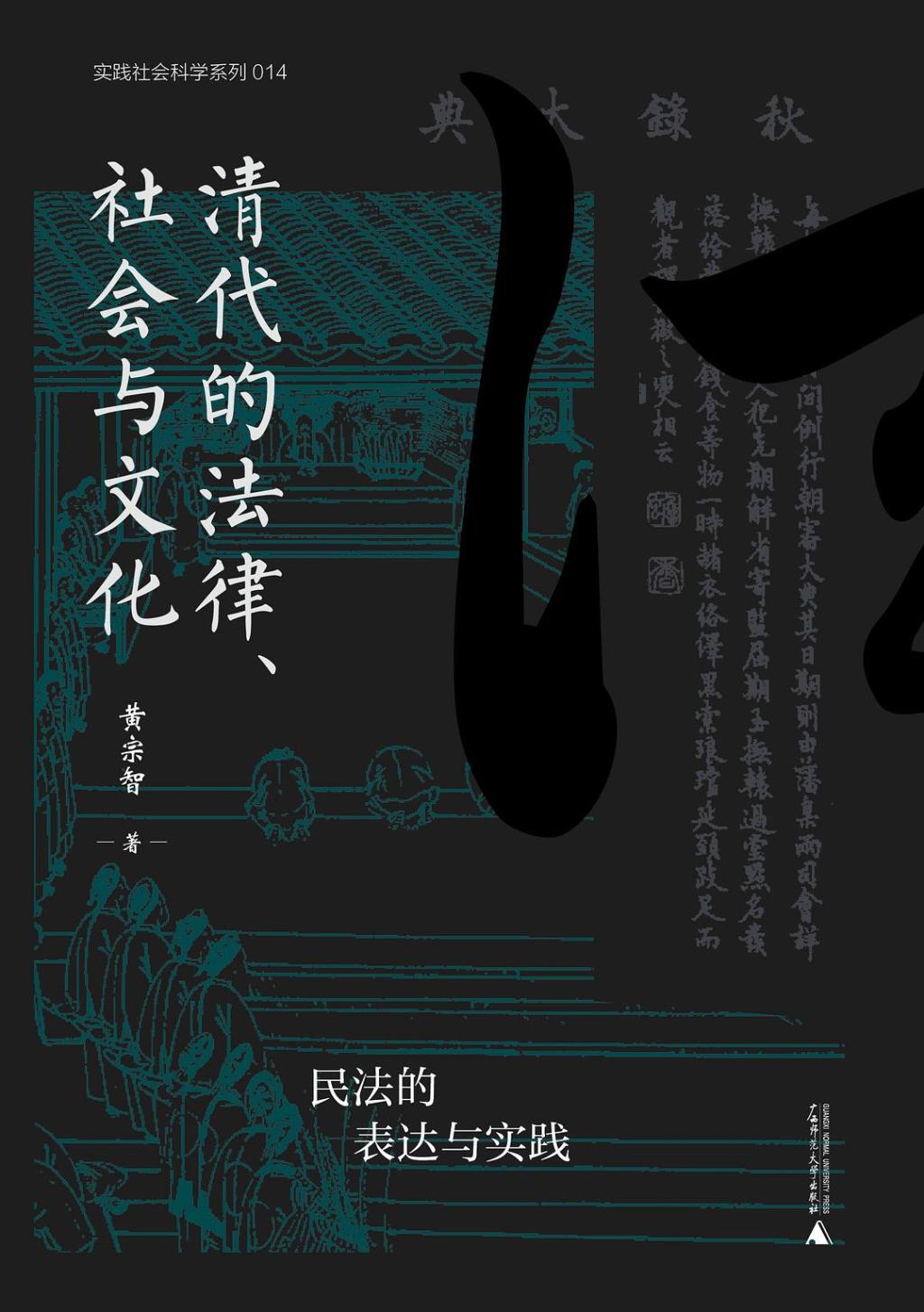
黄宗智著《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面向是作者对城市空间的关注——这可以说是本书一个贯穿始终却并未在标题中体现的主题。我想,作者的这一关怀并非仅仅是出于其师承城市史大家罗威廉教授,亦是源自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的情感联结与居住体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北平,长期陷于经济衰退,市民不得不面对频繁的政权更迭、社会动荡。始建于明代的城墙,将这座城市环绕成一个“巨大的封闭空间实体”,使得“人口只能在城市内部膨胀”(11页)。不过,再坚固的城墙也无法抵抗十九世纪初以来持续的移民涌入。大量外来劳动力迁入,重构了北京的城市空间,在城区内形成了众多的贫民聚居区。而正是在这些低矮杂乱、破旧不堪的城市空间中,本书的主人公们——北平的下层妇女——经历着她们日复一日的生活。
本书的第三章重点讨论了胡同与大杂院这类颇具京城特色的城市空间,以及下层女性对它的理解与利用。尽管在当时的社会改革家与市政官员看来,大杂院不仅是设施破败、缺乏隐私的贫民窟,也是道德暧昧、犯罪滋生的罪恶“温床”。然而,作者却别开生面地指出,对于居住其中的女性而言,这些区域是“妇女与小家庭圈子之外的人进行互动的主要社会空间”(165页),因而也有助于她们构建提供情感支持、处理生活与经济困难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不仅包括日常的友谊与交往,也时常涉及婚外情、性交易,甚至人口买卖等灰色地带。除了胡同与大杂院,二十世纪上半叶交通技术的现代化也为下层女性拓展家庭以外的行动空间、实施弃夫潜逃的生存选择提供了新的可能。在第五章中,作者聚焦人力车、铁路、公路等交通方式,分析道路基础设施如何扩大女性的空间流动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更为庞大且组织化的妇女买卖、商品走私网络。这类网络挑战了国家对城市治安的管控,增加了治理难度;另一方面,也为部分女性逃离家庭提供了现实支持。借此,作者描绘出女性生存手段、城市空间与犯罪行为之间所构成的一组三角关系:对于战时北平的下层女性而言,许多违背主流道德或法律规范的行为,恰恰是她们逃离绝望家庭、争取微小生存空间的生活手段;而特定的城市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为这类行动提供了庇护与通道。
城市空间与妇女生存手段之间所折射出的,正是社会结构与个体能动性之间的关系这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经典议题。作者借用德·塞托的“手段”(tactics)概念,勾勒出战时北平下层妇女在法律与制度间穿梭,有时甚至不得不以犯罪为手段谋求一线生机的无可奈何。这种史家对普通人日常挣扎的捕捉,对被宏大叙事遮蔽的个体生命状态所流露出的悲悯关怀,令我敬佩与动容。然而,我窃以为,正是在这一点上,本书也的确存在继续着力的空间。如果我们将这些生存手段重新嵌入制度、性别与经济结构中审视,不难发现,其脆弱性与暂时性远远超过了其创造性与有效性。尽管作者在书中一再提及女性作为时代与结构变动的“受害者”,称“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是战时北京政治不稳定和长期贫困的受害者”(133页),但在实际书写中,作者的史笔有时会略显过于侧重她们“创造性”地运用制度、游走于法律与秩序边缘的能动性,以至于在个别措辞的使用上可能会引起一些歧义。
例如,在第五章中,作者使用“亚文化”(subculture)一词来描述女性对人口买卖的参与(264页)。尽管他明确指出,这一概念引自美国史学者霍华德·P. 丘达科夫(Howard P. Chudacoff)所著的《单身汉的时代:一种美国亚文化的建构》(The Age of the Bachelor: Creating an American Sub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并解释其意在指涉“主流文化之下的一种情况尚可且无大碍的组成部分”,但在我看来,将“亚文化”一词应用于此,仍值得商榷。我理解作者试图通过这一概念将“妇女买卖”行为去污名化,意在指出,即便是这类通常被视为出卖女性主体性的犯罪行为,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是底层妇女在极端困境中出于生存考虑而作出的自主选择。她们试图利用自身的生育能力、性能力与生产能力等所谓“性别红利”,最大化生存资源,争取生存空间。然而,在书中,这层复杂逻辑似乎并未被明确展开,从而容易引发误解,使读者以为作者是在浪漫化妇女买卖,甚至将其视为一种带有文化认同与自觉的行为。毕竟,在当下的流行语境中,“亚文化”一词常被用来指代某种边缘但积极、独立且具有身份意识的文化共同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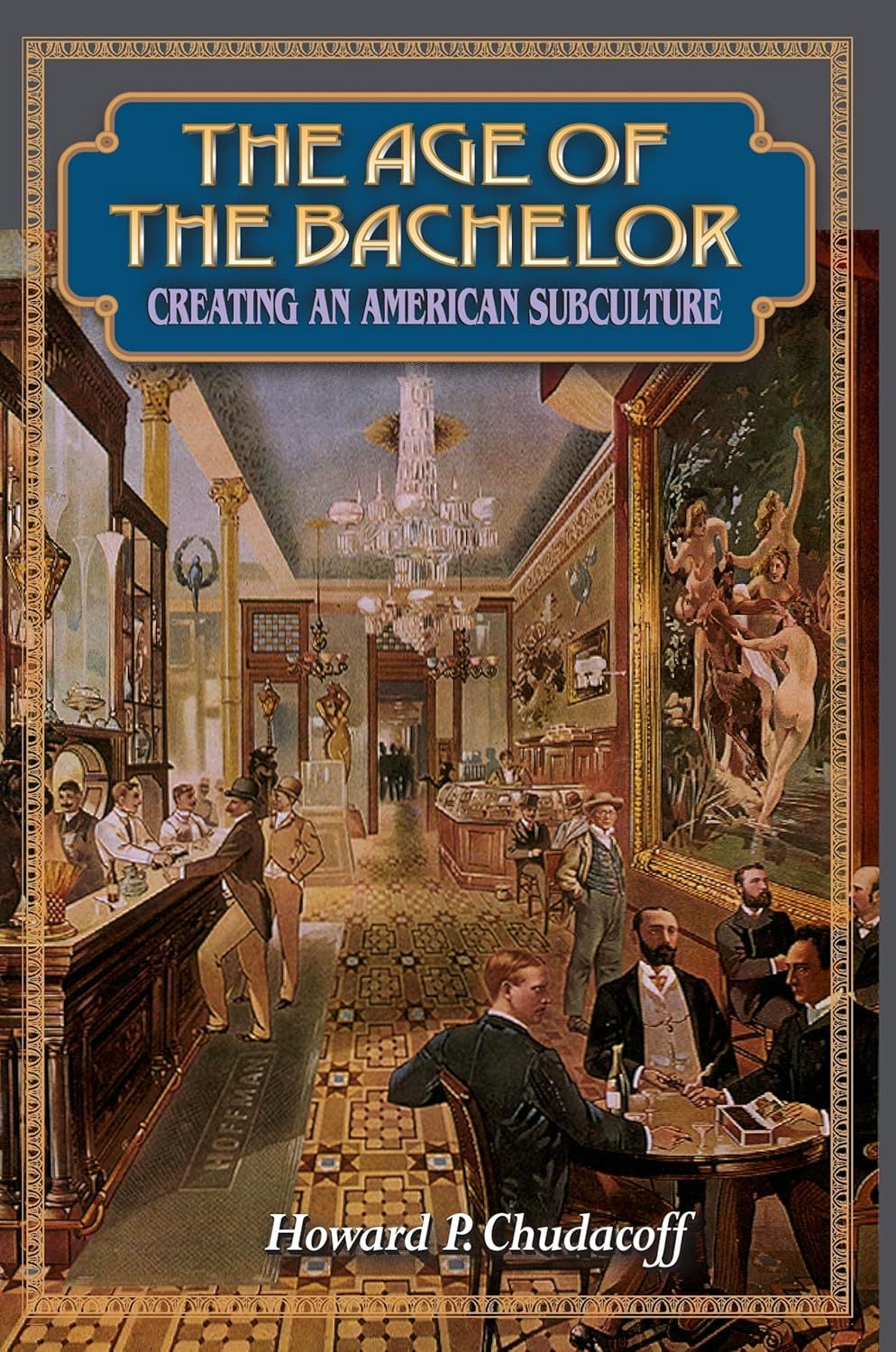
《单身汉的时代:一种美国亚文化的建构》
不过,在我看来,正是作者在“揭示结构性压迫”与“赋予能动性”之间的游移与摇摆,突显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也体现出历史学者在把握史实、权衡立场时所展现出的审慎与克制。因此,在我看来,这本书真正有力的地方,不仅仅在于呈现了战时北平下层妇女在夹缝中求生的生存手段与现实智慧,更在于提醒我们:当我们被这些“手段”所展现出的坚韧与创造力所打动时,不应止步于对个体能动性的赞叹,而要进一步追问——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剥夺、经济失序与伦理压迫,使得这些看似自主的“生存手段”,成为她们几乎别无他途的唯一选项?《弃夫潜逃》这部作品对像我这样的后辈学人而言,是一次深刻的启示,它提醒我们,关注底层妇女的历史,不仅是为了呈现她们的能动性,更是为了帮助后人理解那些能动性为何如此有限,又为何如此艰难。
转载请注明来自夏犹清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本文标题:《郑羽双评《弃夫潜逃》|城墙之下,律法之外:乱世北平女性的生存空间》












 京ICP备2025104030号-15
京ICP备2025104030号-15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